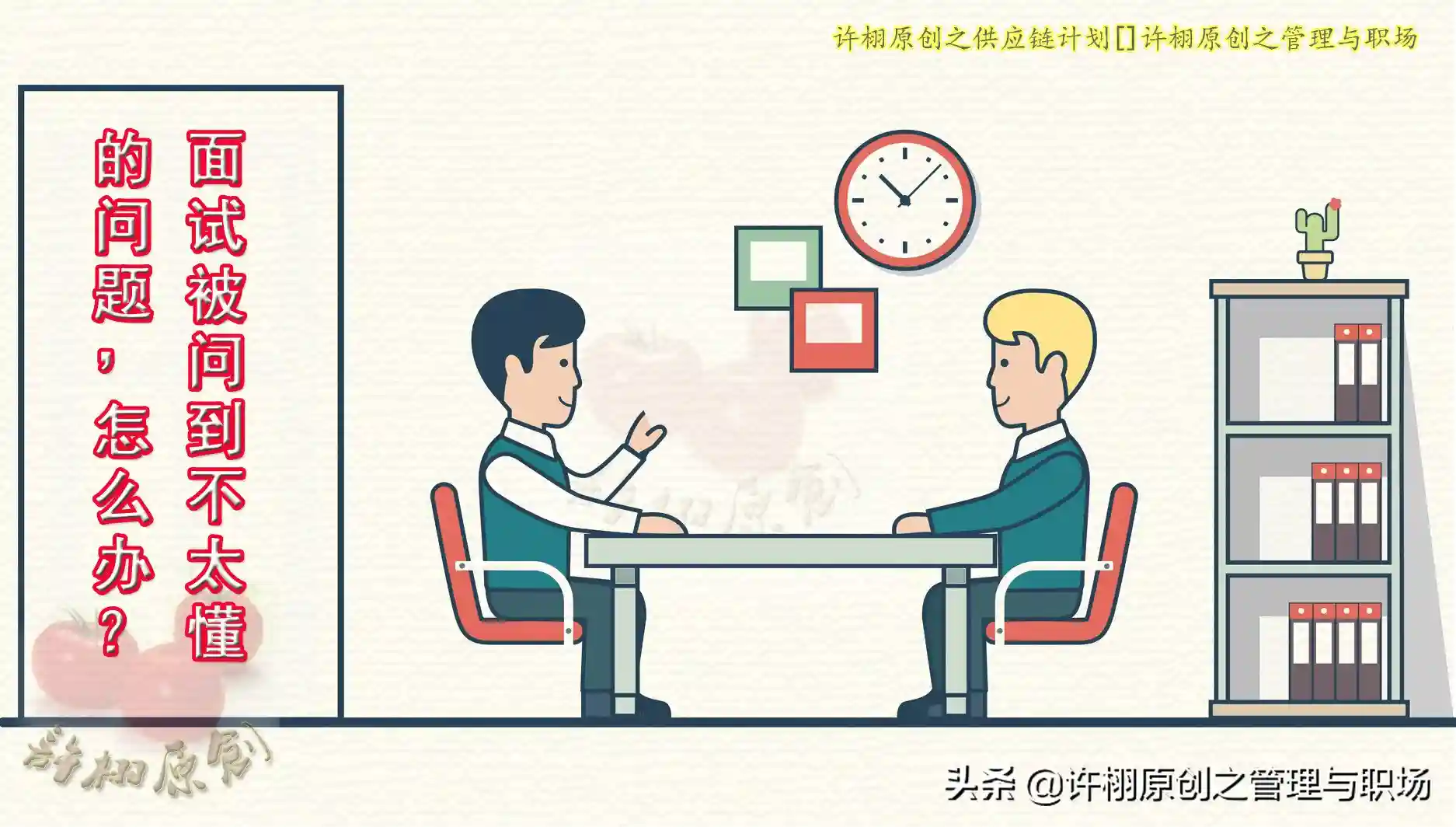■滑溜
小时候,我和弟弟妹妹都很馋。一年到头吃不了几回肉,白面馍馍只有在过年或者别人家娶媳妇生孩子有缘能去才能捞着一次机会。平时,我和村子里的孩子们一样,三餐都以地瓜为食。毕竟,地瓜在当时相比于其它作物产量更高,更能满足我们的温饱。
秋天,地瓜成熟了,几乎每天都是地瓜糊糊;秋后,收完了地瓜,大家就一起去把地瓜切成片,晾晒在地里,或者拉到山坡上,晾晒到䓍窝里,等到晒干后,存起来,随时磨成面粉,可以用来蒸窝头。能够切成片的地瓜叫春地瓜,这样的地瓜煮熟了吃就像蛋黄,香甜而干面,出粉率高。真正用来长期吃的地瓜叫麦茬,也就是在收割了小麦后种植的地瓜,这种地瓜水分大,更糖软,于是我们就把它存到地瓜井里,可以吃过来年的春天。
一天三顿吃地瓜,开始吃觉得香甜,天天吃,就吃腻了,我和弟弟妹妹们就轮流装病。我给母亲说我全身头疼,母亲摸摸我的头:不发烧啊?我便觉得装得不像,就躺在床上打滚,抽泣着摸眼泪。母亲半开玩笑:是不是把牙根吃“黄”了?给你两笤帚疙瘩你就不头疼蛋疼的了。我双手捂着脸,欲哭不能,想笑不行,从手指缝里偷偷瞄着母亲。母亲歪着脑袋,真的拿来了笤帚疙瘩,对着我比比划划,指指点点,举起笤帚疙瘩在半空中猛地一落,向我虚晃一下,被我从手指缝里看到,吓得在床上连滚带爬,挂着泪滴的脸上同时笑了出来。
这时,母亲便会把我揽在怀里,拍拍我的后背,摸摸我的头,对着我们说,走,我给你们滚煎饼去!于是,弟弟妹妹高兴地跳着来拉我,我们便一起捂着嘴咯咯地去帮着母亲抱柴火,挤在锅门前面争抢着烧火。母亲便把那面鏊子重新支好,用抹了油的布擦拭干净,接着去翁里盛了两瓢子地瓜面,加水和了一块盘子大小的面团。
等到我们把鏊子烧热的时候,母亲的面也正好和好了,因为这不是摊煎饼,摊煎饼要把面做成糊,用勺子舀到鏊子上,再用拐子围着整面鏊子拐,这样就可以全部挂满糊。这样做的煎饼做出来厚实、柔软,而母亲的做法是滚煎饼,滚比摊更省事,做出的煎饼薄而脆。在做法上,只要把面和好,但不要把面和的和擀面条包水饺一样硬,更不能和的和摊煎饼一样的稀软,所以要把握好度,让面达到即成块状又比较摊软才可以让面挂到鏊子上。火燃得越来越旺,母亲便把那块大面团放到鏊子上,双手推着面团往前滚,伴随着哧溜哧溜的声响,热气如漂着白云立刻弥漫着整个厨房。随着母亲把面团转完一圈的功夫,鏊子边缘上的煎饼都卷了起来,香味扑鼻,我们不眨眼地盯着第一个出炉的煎饼,不停地咽着口水,为了掩饰自己的“馋”,我们几个孩子开始相互指责对方是个馋猫,看到煎饼就拔不动腿了。
母亲快速地揭起煎饼,小心翼翼地折叠着她的杰作,那圆圆的大煎饼被她几下叠得有梭有角。
做出来的第一个煎饼当然是我的,这毕竟是我用“头疼”挣来的战利品。我咬一口,他们就眨巴一下嘴巴,再咽一口口水,于是,我就把我咬过的,让他们轮流咬一口,个个看着我,过年领了红包一样的开心。尽管当时没有咸菜,也没有大葱,但萦绕在心头的就是那股说不出来的煎饼香味。
不知道那面鏊子何时来到我家,也不知道它已经在我家呆了多少年,只要我想弄点好吃的解馋,总先想到那面鏊子。要么洒点油煎个鸡蛋,要么烙些小油饼。数十年过后,电已经普及,电饼铛入户,不需要母亲亲自去烧火烙饼,但就在那个年代,虽然我们一家人仅仅以地瓜为食,因为有了母亲,有了那面黑不溜秋的鏊子,有了那面鏊子上的酥脆飘香的煎饼,牢牢地把我拴在那个曾经的童年味道里。
仿佛,老家的母亲又蹲坐在灶屋里,那面熟悉而又陌生的鏊子下面燃起一堆篝火,煎饼的香味抵挡不住地向我飘来……
【编辑制作:滑溜,本名刘健。憨派文学创始人,著有憨派文学奠基之作《滑溜》一书。《中国憨派文学》主编。中国散文学会会员。】
《中国憨派文学》:
邮箱:884714466@
壹点号《中国憨派文学》
新闻线索报料通道:应用市场下载“齐鲁壹点”APP,或搜索微信小程序“齐鲁壹点”,全省600位记者在线等你来报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