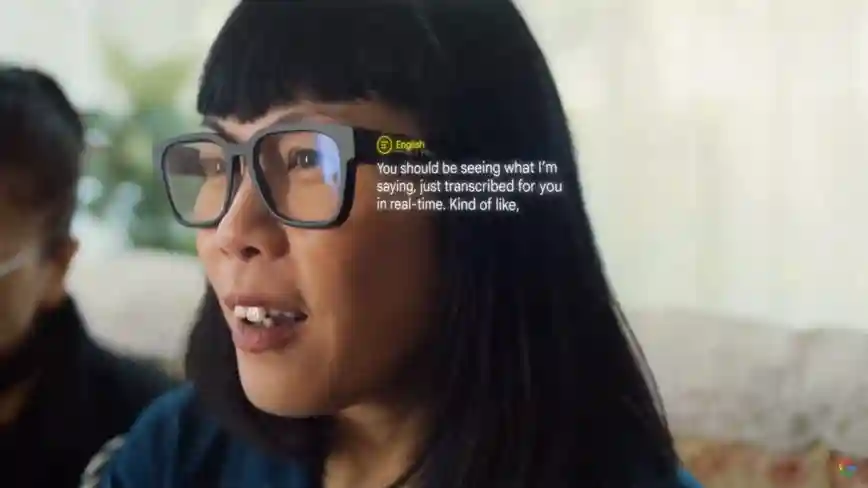(一)鳏寡孤独,语出《孟子·梁惠王下》:“老而无妻曰鳏,老而无夫曰寡,老而无子曰独,幼而无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穷民而无告者。”本指四种类型的人,因其相似的一点就是,他们都是社会的弱势群体,是“天下之穷民而无告者”,所以,到后来,这四个字就用来泛指没有劳动能力、生活上无依无靠的人。
我在本篇所要讲述的,就是属于这个群体当中的几个人。
在我们生产队,有一个名叫万山的老头,就是一个鳏夫,也就是老光棍。他是村里的“五保户”。
此人姓啥,整个队里的人都不知道,大家都叫他万山子,大概“万山”该是他的名字吧。从我们小孩子来说,由于年龄、辈分等的差距,他至少是我们父辈一代的人,所以,我们小孩们,都应该称其为“万山叔”才对。但在我的记忆中,好像没听过有小孩称呼他“万山叔”,都是直呼其名的。
在我的印象中,万山叔似乎是一个神秘的存在:哪里人?多大年龄?都不知道。唯一了解的,就是此人孤身一人,形单影只,孤苦伶仃。住在一间破旧的房子里,夏天漏雨,冬天漏风。家里阴暗破旧,除了几副碗筷,别无长物,真可谓是家徒四壁。自己常年不洗脸,面目黧黑,衣服也是脏兮兮的,看不出本初的颜色。
那时候,生产队里所有的社员,都要参加队里的各种生产劳动,但万山叔就是一个例外,我也不知何故如此。他每天的事情,就是给队里的各家各户挑水。不论刮风下雨,春夏秋冬,没有一天间断过。我就见过在下雨天,他淋着雨,给人们挑水的样子。他在自带一个洋磁碗,别在腰间,去给人挑水。每进到一家院中,把水倒进水缸,盖好水缸的盖子。这时,主人就会端出些吃的东西来,倒入他自己准备的碗中,然后,他就离开了。有时候,主人请他回屋里坐坐,他是万万不肯进去的。回到自己的家里,就把人们给的东西热一下,吃了。天天如此,月月如此,年年如此。
在那样是年代里,万山叔就是一个别样的存在。
寡,即寡妇,指丧夫的已婚女性。旧称“未亡人”。
在我家的巷子里,就有这样一位老太太。本名不详。在过去,女性自己往往连一个正式的名字都没有。未嫁时,一般按其在家里的排行来称呼,如大女子、二女子、三女子等等。即使是有正式的大名,也一般不用,所以别人也不知道。出嫁后,人们习惯以其丈夫的姓氏,加之这位女子在丈夫家族中的位次来称呼她,如王婶、李大大(伯母)等。我要说的这位老太太,我们就称其为“二元老太太”,因其丈夫叫贾二元。
记忆中的二元老太,大约七十岁左右,小脚,走路颤颤巍巍,但也还精神。花白的头发,常年梳一个那时候老太太们的“标准圆发髻”。掩襟外套,非灰即黑,再无其他色彩,倒也干净整洁。那时候,她已年龄偏大,不再去地里参加生产劳动了,但生产队场院里的一些轻活,她有时也去做会。身体很好,极少看见过她生病。
老太太早年丧夫,一直是自己一个人带大二男一女三个孩子。三子女都已成人另过,她自己一个人独立生活。大儿子原来与她同住一个院子里,但关系似乎不洽。后来搬出去另住,加之家庭矛盾,到后来竟与其母断绝母子关系,这在当时的村里,成了一条惊人的消息,闻之者无不骇愕;二子招工,远赴阳泉,也不能守亲尽孝;一女在不远的邻村,偶来走动,也不甚勤。老太太一个人生活,倒也简单清净自在。
记忆所及,印象很深的,是老太太的节俭。
其实,老太太远在阳泉的二儿子,还是很惦念在老家的母亲的,也经常寄钱给母亲。但老太太却舍不得花钱,这,大概也是她们那一代曾经经历过贫穷和苦难的人的共性吧。每到傍晚掌灯时分,老太太就来我家坐着闲聊。一年四季,几乎天天如此。后来才知道,她之所以每天要来我家闲坐,一来是为了给自己解闷,二来更重要的原因,是为了“省灯”。在她自己的家里,几乎没有亮灯的时候,怕费油费电,当然也就费钱。所以,天天来我家,就是为了“蹭灯”。很多时候,我们做好了饭,也就一起邀老太太吃。经常在一起,很熟了,如同家人。
不仅是“蹭灯”,其实,在冬天的时候,更是来“蹭暖”。谁能想象,一个大不生火做饭,不生炉火的屋子会有多么冰凉!据老太太自己说,她的锅台上,冬天都会结冰的,把碗放在上面,居然打滑。自己的鸡产的鸡蛋,自己从来不舍得吃一个,都要卖掉,换几个零用钱。
生活中,老太太最开心的事情,就是她与儿子之间的书信往来。
当时,我是我们巷子里的“读书人”,老太太儿子来信回信,自然也就成了我的事情。她不识字,每有来信,她颠着小脚就来我家了。一进门,就急不可待让我给她念信,看她儿子又和她说些什么。信是书面语,我还得把信上的内容,“翻译”成家常用语,说给她听。她耳背,说话得喊。经常是误听误解,等最后明白过来,又哈哈大笑。老太太最快乐的时候,也就是我给他读信的时候。
读完了信,还有回信。我当然责无旁贷。同样,我要把她说的事情,“翻译”成书面语写下来。来的时候,就准备好了回信用的纸、信封、邮票等。写好后,还须再完整念一次给她听。其中有什么需要修改的地方,再次询问证实后,才最后定稿。那时候,一封信往返的一毛六分钱,是母子之间最有意义和价值的付出。
后来,我外出读书,离开了村子,也就少了很多与老太太的接触。只知道她晚年,被儿子接去阳泉生活,并在那里去世,得以善终。多年后,她儿子偶回村里,我们难得一见。谈起往事,不胜唏嘘。
说到“鳏”,队里还有一位老者,记忆深刻。
此人姓宿,名喜堂,五十多岁,放在现在,还算中年,但在那个时候,看上去也就似乎是个老人了。他没有妻女,孤身一人,和弟弟一家住在一个院子里。他有手艺,会钉鞋。村里有谁的鞋需要修补,就去他那里。修了鞋,也不说价格,修鞋者随意放几毛钱就行。他也就是靠着这个小手艺,自己才能有点零花钱。很多时候,甚至分文不取,义务修理。有孩子们去了,一定会拿些零食出来给吃的。他的身世我不知道,但在那时候,街坊邻居们都知道,他有个相好的女人,时间长了,人们也就不再有啥闲言碎语了。生活一如既往,波澜不惊。生活中,他喜烟、嗜酒,无人时,自斟自饮,逍遥快活;有友来,则对饮闲聊,腮红筋突。活得很自在。除此而外,他还会钉马掌,队里的骡马驴等大畜的铁掌,也都是他弄的。因为有此技术,所以,他去地里劳动的时候也就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