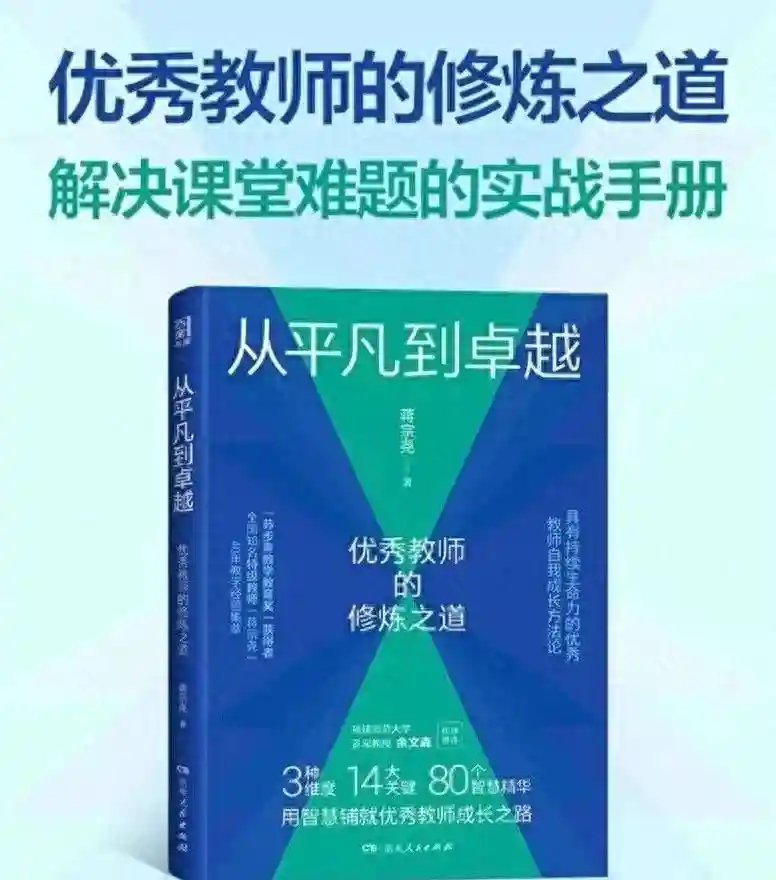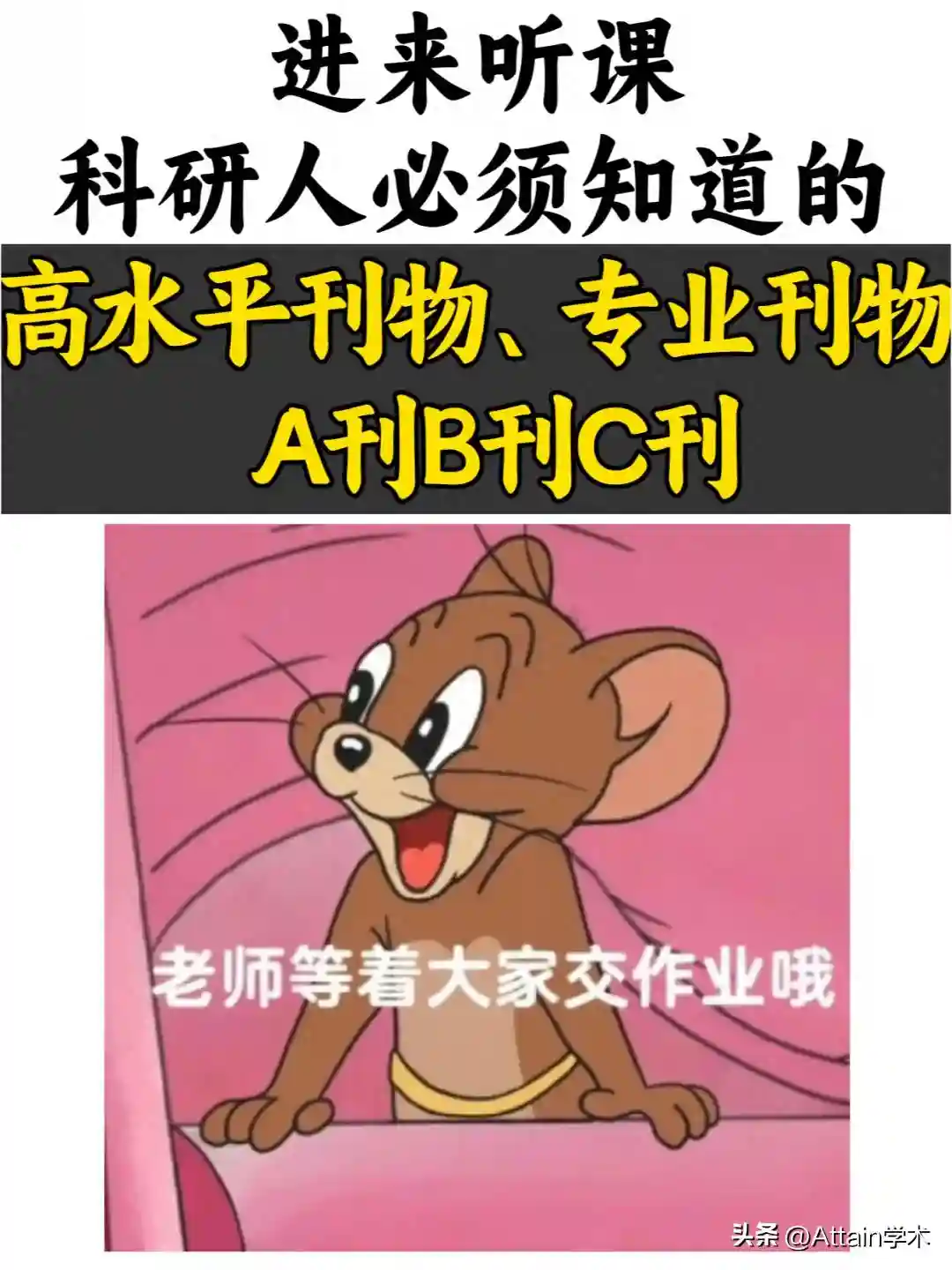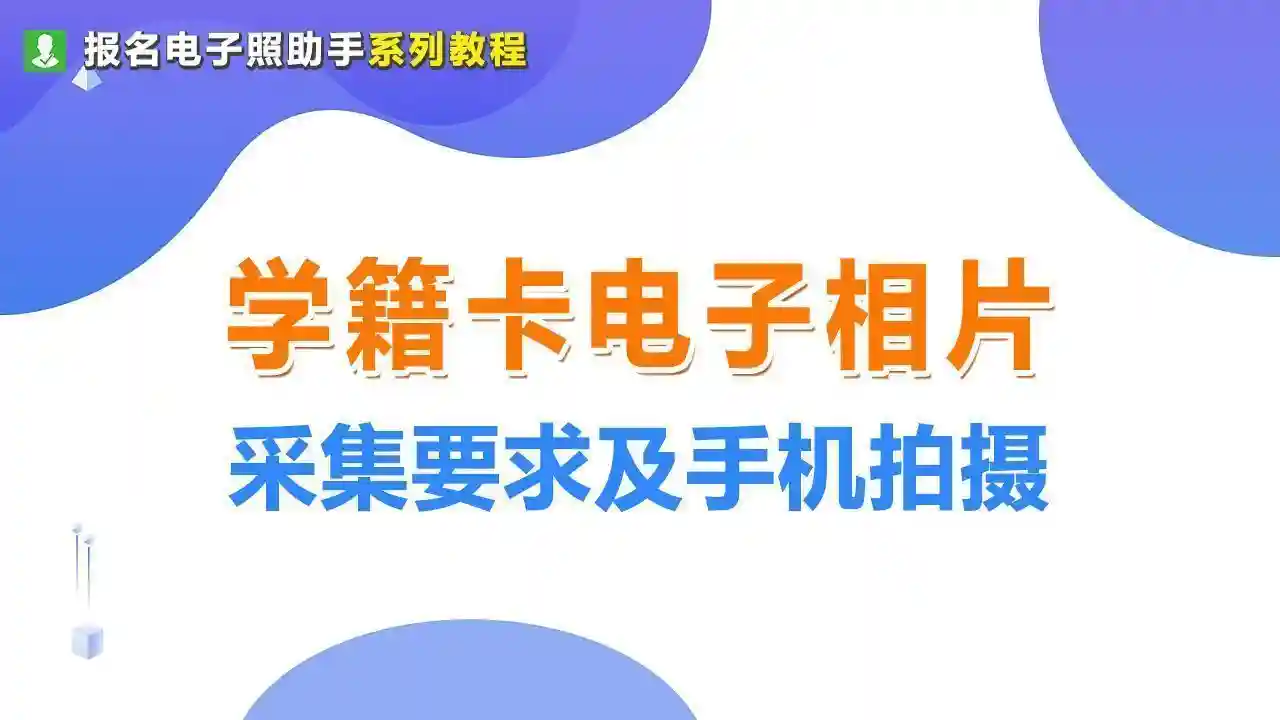国际先驱导报7月13道还未踏上这片土地时,脑海中一直闪现着乌兹别克斯坦(以下简称乌兹)可能的模样。
兴许它有几分悲凉吧?毕竟是胡天胡地胡风胡舞的西域边陲,埋葬着太多西征将士的尸骨,风干了太多中原流亡者、和亲公主思乡的眼泪;兴许它有几分好战吧?数百年来民族间胡征互伐,残酷倾轧,不知帖木儿大帝的一代代子民如今是否还有称霸中亚的野心?
它必十分恢弘吧?帖木儿穷尽一生力气建造的撒马尔罕该是如何的动人心魄;它必是多元的文化高地吧?丝绸之路上的声声驼铃带来了商品融通,也带来了中原、波斯、突厥和欧洲文化的汇集、交流、融合;数百年后海路兴起,丝绸之路转向日落黄昏,日渐衰微的王国沦为英俄的势力争夺范围,该是何种的悲凉?
俄人统治百年后,骄傲的乌兹人迎来独立,他们定是充满骄傲吧;然而四邻强大,处在欧亚咽喉的乌兹想要站稳脚跟,也并不容易吧?
热风如烧的六月,带着所有想象,笔者终于来到了这片神秘厚重的土地。
千年古国擅美食
才不是八月飞雪,万里流沙的苦寒之地,千年古国乌兹分明是受神明眷顾的绿洲之国。
首都塔什干像极了一个古老精致、大气华贵的雕花漆盒,盒子的每一处都收拾得干干净净,没有一丝积垢。锡尔河从天山奔流而来,灌溉着这片土地,给这座日光之城带来盈盈绿意。宣礼塔高耸着,在干爽蓝天和黄色山脉的映衬下越发肃穆。古朴的清真寺静静地等待着它的朝拜者,阳光下,蓝色的琉璃瓦和金色的花边衬着土色砖墙,显出最悦目的颜色。
北边的老城,处处古迹,处处美丽,她大方恬静淳朴庄重,充满了诗情词韵。南边的新城,八街九陌,车水马龙,有宽阔马路,摩登商厦和穿梭地铁,自有中亚大国的气宇轩昂、非凡气度。城里也留下了许多苏联时期的楼房,和闪着金光的东正教堂。
如火六月,大街上鲜有行人,有一地却是人声鼎沸。
何处?即是乌兹首屈一指的中亚抓饭中心。
隔着街就闻到了扑鼻的香味,心都跟着痒了起来,唾沫更是咽下了好几口。凉棚下的阴凉里,厨师小哥们顾不上四脖子汗流,忙着切肉蒸饭。羊肉被烤的金黄发亮,剔骨、再切成小块。一旁的大铁锅里,羊油把米饭染成黄色,溢出阵阵香气。
接下来就是苦工了。小哥拿着长勺在铁锅里不停搅拌,直到羊肉、胡萝卜、黄椒、洋葱、葡萄干的味道沁入米饭。蒸上四十分钟,一碗彪悍英武的羊肉抓饭就出锅了。加入剥好的鸡蛋鹌鹑蛋各一个,铺上几片马肉,可真是分量十足。色彩鲜亮的抓饭和圆圆的馕一起,配上一碗西红柿洋葱沙拉,再来一杯凉争冰雪甜争蜜的冰镇樱桃汁,真是人间至味!
不知为何,眼前这盘抓饭竟没有一丝膻味。问问身边的老中亚们,才知抓饭的原料是小绵羊,不仅肉质细腻,易熟,而且没有膻味,无比滋补。
抓饭罢,剖个西瓜,再端上苹果、杏子、甜瓜、沙枣,美极!
声名远播的抓饭,加上誉满天下的拉条子、烤包子、鸡肉面条汤,这些名吃让乌兹菜在中亚早早就树立起霸主地位。看看莫斯科人头攒动的乌兹餐厅,便知道乌兹菜系的美味和流行了。
都说地方如人,有着自己的性格,我想塔什干一定是位俏丽的姑娘,阳光把她照得暖暖的热热的,好让她的内心存不下一丝阴暗。她笑靥如花,明媚晴好,热情如火。她舞姿极好,轻舞罗衣如回雪飘摇,美好的足以让旅人们忘了身在异乡。
晚上七八点钟,骄阳谢幕,夜晚降临。空气凉飕飕的,人们或街头纳凉,或酒肆小酌,或舞池起舞,享受着片刻自由欢愉时光。夜色如水,笑语声、歌舞声、笛声和山风声、流水声交相呼应,奏出一曲别样的乌兹小夜曲。
人间物类无可比,君今不醉欲安归?不如就留在这塔什干的美好夜色吧!
充满智慧的游牧民族
从前总认为华夏文明首屈一指,西域皆是“穹庐为室旃为墙,以肉为食酪为浆”的蛮夷之地。在乌兹走走停停,越是靠近,越是感受到自己的浅薄与无知。
在撒马尔罕金碧辉煌的帖木儿家族陵墓,一生叱咤方逑的帖木儿大帝将自己老师的棺木摆在他的棺冢之前。
“国将兴,心贵师而重傅。”从德里到大马士革,从咸海到波斯湾,帖木儿能在30年的时间建立横跨中亚和地中海的大帝国,想来依靠的不仅是杀伐决断,更与他虚怀若谷的尊师之风密不可分。
帖木儿家族的铁蹄响彻之时,这个帝国的统治者也不忘仰望星空。
在宫殿如繁星,城垣若太阳的撒马尔罕,帖木儿之孙兀鲁伯修建的天文台静静矗立在城市最高点。
兀鲁伯在位30年间,天文台测定了1000多颗星辰的方位,成为继古希腊天文学家后,测定星辰位置的最准确的记录。
不得不对这个充满智慧的游牧民族刮目相看。
身处中亚心脏,丝绸之路必经之地的绿洲之国,我才知道玄奘当年经过的这个地界绝非飞鸟千里不敢来的不毛之地,而是物产丰饶的瓜果之乡。
当然,让我最觉震撼,冲击最大的便是我们引以为傲的华夏文明,原来吸收了如此多的西域元素。从苹果、石榴、葡萄、胡椒、胡桃、菠菜、苜蓿,到笛子、琵琶,我们每一个中原子民都享用着丝绸之路带来的千年红利。
如今,当峨冠博带零落成泥,崇楼华堂失了色彩,唯有交流带来的文明成果穿越时光深深地刻凿在我们后人身上,也告诫着我们开放才有进步,闭关锁国永远是弱国之举。
以圆融的平衡外交自处
乌兹行结束之时,行前的几个问题似乎有了些眉目。
东方文明眼中的西域悲凉吗?或许有一些。然而对于那些想要把路走得远一些,更远一些的商旅和行脚僧而言,西域远非边塞诗中的愁肠之地,这里是他们向未知探险,豪迈壮行的新起点。
绿洲子民好战吗?历史的长河里,善于经商的他们恐怕只祈盼这条丝绸之路上不再有政权更迭、你争我夺,不再有烽火狼烟和远征的军人。
帖木儿的后人们今雄心安在?答案是肯定的。从1916年中亚民族大起义开始,乌兹便对民族独立孜孜以求。苏联解体后,国父卡里莫夫更是筹谋着复兴大业,首都塔什干被建设的繁华摩登,乌政府也在雄心勃勃地大力推广母语乌兹别克语。
周边大国林立,内陆小国如何自处?独立后,乌兹人奉行着圆融的平衡外交。谁让他们是丝绸之路上精明的商人之后呢?
离开乌兹的夜晚,一个人走在塔什干街头。满街的雪弗兰车从身旁呼啸而过,街上的姑娘用英文热情地为我指路,帖木儿广场上,跛脚大帝跃然马上,带领着他的后人策马向前。(本报记者发自塔什干)